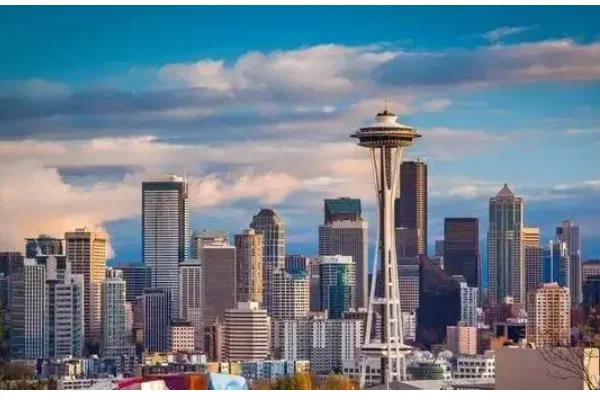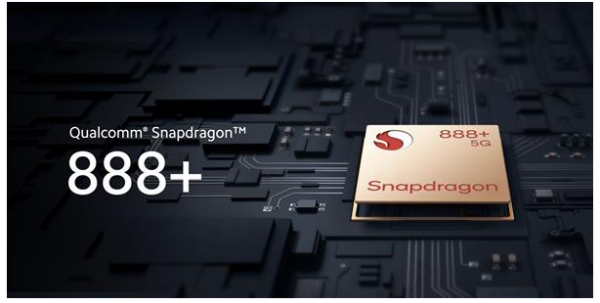红楼梦里最诡异的人物(红楼梦里最恐怖的人)
红楼梦里最诡异的人物
分别是秦可卿、净虚、妙玉。
1、秦可卿
秦可卿作为贾府的长房长孙媳妇,在家中的地位很高,但她却与家公贾珍发生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,被发现后选择了自尽,但秦可卿死得蹊跷。通过她的判词可以推断出她的死有可能跟贾珍私通有关。

2、净虚
这是她的法号,作为尼姑的他不好好的修行,反而插手世俗之事。净虚是典型的收钱办事,把金钱看得比人命还重要的人。

3、妙玉
妙玉的出场不多,但她的身世是个谜,这个明明和贾府没有关系的人却能位列金陵十二钗,每次出场贾府都将她奉为座上宾,从妙玉的用行可以看出,她并不是普通的人家,有人猜测她有可能是皇室,或者是前朝公主。

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分别是:
贾、史、王、薛,四个家族,即是指以贾府为首的一个封建官僚集团。他们势力庞大,都名列当时的“护官府”之中。这四家皆连络有亲,一损皆损,一荣皆荣,扶持遮饰,俱有照应的。贾——贾不假,白玉为堂金作马。
主要人物:贾宝玉、贾琏、贾珍、贾政、贾家四春,是红楼梦中主要描述的家族,也是红楼主要情节的发生地;史——阿房宫,三百里,住不下金陵一个史。
主要人物:贾母、史湘云,红楼梦中没有直接描述,只是间接描述了史湘云的叔婶;王——东海缺少白玉床,龙王来请金陵王。
主要人物:王夫人、王熙凤、薛姨妈,与贾府建立了主要的姻亲关系;薛——丰年好大雪,珍珠如土金如铁。主要人物薛蟠、薛宝衩,相对其他三府,薛家官不大,但是最有钱。
红楼梦里最恐怖的人
红楼梦里最恐怖的人:曹公给这个水月庵老尼取名“净虚”,也是明着的讽刺。净虚:净,实乃虚也。佛门六根清净,然净虚不净。所谓六根,无非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眼贪色、耳贪声、鼻贪香、舌贪味、身贪细滑、意贪乐境。净虚一根不符。
净虚老尼,佛口蛇心,刁滑世故。虽吃斋念佛,但手里却积攒了数条人命。张金哥和守备之子自尽,固然是凤姐弄权,但也和净虚脱不了直接干系。她主持贾府的家庙,频繁出入荣府,投乖卖巧,只为讨主子一笑,进而行便利之事。
一个出家多年的老尼,偏要管红尘男婚女配之事,本就很讨厌了。更讨厌的,她还要棒打鸳鸯,拆散一对有情人。张金哥和守备之子之死,固然是自尽,但首要的罪魁就是净虚。没有她假充能耐掺和事儿,见钱眼开,去求荣国府爱显摆的凤姐儿,悲剧不会发生。
出家人以慈悲为怀,可在净虚的眼里,收下了长安府太爷的银子,那看什么都比人命重要。休说是出家人,就是一般世俗之人干了这般伤天害理的事,也会夜夜难眠良心不安,嘴里念阿弥陀佛的。可净虚压根没放心上,白天装模作样念经,晚上去贾府谄媚逢迎。时间一长,连带着她的徒弟智能、智通都和贾府的人混熟了。
那秦钟是宁府的亲戚,因智能常来玩耍,二人熟稔的以至发生了一段风月。红楼之一十五回,凤姐带着宝玉秦钟往馒头庵,入夜,宝玉寻秦钟,亲见他和智能实实在在地滚到了炕上,且“正在得趣”。
下面分享相关内容的知识扩展:
在《红楼梦》里面,为什么宝玉扔了玉项链后就神志不清
《红楼梦》第九十五回:“因讹成实元妃薨逝,以假乱真宝玉疯癫。”在这一章中,因为宝玉的“通灵宝玉”诡异的丢失不见,怡红院的丫头婆子们以及贾政夫妇、凤姐等人,都万分恐慌。以为这是大凶之兆,丢了“命根子”哪还有命在?恐怕宝玉的性命安危也会受到威胁了。

宝玉在这块玉有灵性或者不丢失的情况下,代表他在自己的世界中,被玉保护着他所思所想,他所认为的世间万物的准则。那么当玉丢失的时候,这个庇护他的空间消失了。他的思维观念和浊世冲突,污浊侵蚀了他,所以他才会变得疯疯魔魔的。

宝玉身上那块通灵宝玉是非常重要的一样东西,那玉是女娲炼石补天所遗留下来的,又是宝玉含在口中而生,是具有特殊灵性的,在第二十五回“魇魔法姊弟逢五鬼”就写了,宝玉中魔是因为通灵宝玉失了灵性,如果没有玉的庇护,宝玉就很容易为鬼邪所害(红楼梦里有很多隐申含义,需要仔细琢磨)。由此可见,那块玉有多重要,如果失了玉,宝玉就会失了心智。

作者给顽石的幻相命名为“通灵宝玉”,中含“通宝”二字,正是帝位的隐语。因为古代货币正是铸以“通宝”及帝王年号字样的,如“乾隆通宝”之类。通灵玉刻文“莫失莫忘,仙寿恒昌”,《三国志吴志》载:“传国玺文曰:受命于天,既寿永昌。”可知通灵玉之文有意模仿传国玉玺之文以示其帝位象征的内涵。
在红楼梦里,王熙凤和贾琏一共生了几个孩子?



这可能是曹公的一个疏忽,巧姐,大姐和刘姥姥有莫大的关系。

第四十二回:刘姥姥二进荣府,逛大观园,王熙凤的女儿大姐,生病,刘姥姥指出怕是遇见什么神鬼,结果法事做后,大姐儿病好了。这是刘姥姥之一次救助大姐儿。
王熙凤之后请姥姥起名:因为大姐出生这一天,七月初七,不吉利,姥姥以毒攻毒改大姐儿为巧姐。这是明显大姐和巧姐为一人。

我们再从一个角度论证:刘姥姥二进荣府:
板儿与巧姐互换佛手、柚子顽一段(庚辰本第四十一回),旁有两段脂批。一云:“小儿常情,遂成千里伏线。”一云:“柚子即今香圆之属也,应与缘通,佛手者,正指迷津者也,以小儿之戏,暗透前后通部脉络,隐隐约约,毫无一丝漏泄,岂独为刘姥姥之俚言博笑而有此一大回文字哉”。可以看出和刘姥姥有缘之小孩就是巧姐。
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两个小孩的名字一起排列:
原文第二十七回,芒种时节,且说宝钗、迎春、探春、惜春、李纨、凤姐等并巧姐、大姐、香菱与众丫鬟们在园内玩耍,独不见林黛玉。
在随后的第二十九回贾母带领家下众人去清虚观打醮时,大姐和巧姐同时出现了。
凤姐儿的丫头平儿、丰儿、小红,并王夫人两个丫头也要跟了凤姐儿去的金钏、彩云, *** 抱着大姐儿带着巧姐儿另在一车,还有两个丫头……
而我们再回过头来想一下,刘姥姥改名字在第四十二回,但在这之前却出现了巧姐这一名字,书中第二十七回,第二十九回分别出现,大姐和巧姐。这个说明了曹雪芹的一个疏忽。

但事实更为诡异:
程本第二十九回: *** 抱着大姐儿,另在一辆车上。
程本第二十七回:且说宝钗、迎春、探春、惜春、李执、凤姐等并大姐儿、香菱与众丫环们,都在园里玩耍,独不见黛玉。
那么是什么原因呢?有可能是曹雪芹一开始构思的时候是有两个小孩巧姐,大姐,
但后来为了情节需要曹雪芹只留下一个小孩。这一决定是曹雪芹写到后面才决定的,但是曹雪芹是边写边改边流传,批阅十次,增删五次,红楼梦前面章节没改好,就流传出去,那么有可能之前没把巧姐在第二十七回,第二十九出现去掉就流传出去。
红楼梦里面说的"意淫"到底是什么意思?
红楼梦里面说的"意淫"到底是什么意思?还有,宝玉送黛玉旧丝帕是什么意思?相思吗?
意淫 语出《红楼梦》第五回 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饮仙醴曲演红楼梦
警幻道:“... ...如世之好淫者,不过悦容貌,喜歌舞,调笑无厌,云雨无时,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兴趣,此皆皮肤淫滥之蠢物耳。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,吾辈推之为‘意淫’”。 关于“意淫”的解释,警幻仙子又说:“‘意淫’二字,惟心会而不可口传,可神通而不可语达... ...” 可见是一种境界,除了贾宝玉,再没有第二人可以当之无愧。警幻仙子早就说了:“吾之爱汝者,乃古今天下之一淫人也!”目前这个词的用途非常广泛,涵盖了希望、憧憬、梦想、发呆、诡异的笑、心理犯罪、偷窥、臭美等等一系列的内容。碰到老熟人就可以打招呼:“今天你‘意’了没有啊?” 不用担心冤枉好人。
====
究竟什么是“意淫”,仅凭《红楼梦》书中的某段只言片语去推测,都有盲人摸象之嫌,正确的研究 *** ,应该是把《红楼梦》中关于“意淫”的表述综合起来,加以归类分析,从总体上对“意淫”加以全景式地把握。
1.“意淫”首先是“淫”,《红楼梦》作品主人公是“天下古今之一大淫人”!作者首先借“警幻仙姑”之口,说明“好色即淫”,“知情更淫”,所谓“好色不淫”、“情而不淫”,都是“轻薄浪子”“掩非饰丑之语”。所谓“天下古今之一大淫人”,也就是在时间和空间上,对所有“淫人”加以比较,《红楼梦》作品的主人公最“好色”,最“知情”。
2.“意淫”不是“皮肤滥淫”,不是生活中男女之间肉体上的结合,不是《红楼梦》书中贾珍、孙绍祖、多姑娘等人的 *** 行为。作者告诉我们,“淫虽一理,意则有别”,“意淫”是精神层面的“淫”,是“天分中生成”的“一段痴情”,同“世之好淫者”有着本质上的差别。对那些“悦容貌,喜歌舞,调笑无厌,云雨无时,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性”者,作者统统斥之为“皮肤滥淫之蠢物耳”!
3.“意淫”可意会而不可言传,奥妙所在,存乎一心。由于“意淫”是精神层面的一种生活态度,所以作者告诉我们,“可心会而不可口传,可神通而不可语达”。这里所说的“心会”、“神通”,就是内心对“好色”、“知情”的一种领悟。这种领悟只存留于精神层面,而不可应用到肉体上,一旦付诸肉体实践,则变成了“皮肤滥淫之辈”。
4.持“意淫”生活态度者,是女人的朋友,但又为社会所排斥。作者明确告诉我们,“独得”“意淫”二字之真谛者,在“闺阁中”“可为良友”,可以“独为我闺阁增光”。但一入此道,便“未免迂阔怪诡”,“百口嘲谤,万目睚眦”,为社会(主要是上流社会)所不容,终不免“见弃于世道”。
5.社会上持“意淫”生活态度者,不是“情痴情种”、“逸士高人”,就是“奇娼名优”。他们既非“应运而生”的“大仁”,亦非“应劫而生”的“大恶”,“其聪俊灵秀之气,则在万万人之上;其乖僻不近人情之态,又在万万人之下”。作者通过贾雨村之口,开列了一大堆此类人名单,如陈后主,唐明皇,宋徽宗,柳耆卿,唐伯虎,李龟年,卓文君,薛涛,崔莺等。
从以上五个层面的分析,我们可以作出如下推断:所谓“意淫”,就是文学作品中的“情”,戏剧舞台上的“淫”!这种“情”和“淫”,就是文学生涯中的“情痴”、“情种”,体现的是作者精神层面上的一种境界,而不是作者本人的肉体活动;这种“意淫”作品,当然为市井小民、闺阁红楼所欢迎,但同时又必然与以程朱“理学”、王陆“心学”为正宗封建正统伦理道德发生冲突。
有人可能要问,既然是文学作品,不论小说还是戏剧,都是“口传”、“语达”的,出自作者之手,入于读者(观者)之目,为什么说不可“口传”、“语达”呢?这里说的不是作品本身,而是作者的创作态度。作者把心中的“情”和“淫”,用什么方式表达,表达到什么程度,表达出何种境界,确实是只能“心会”、“神通”的精神活动,无法为外人道的。古今中外所有的名作家,创作时心中激荡的那种“情”,谁说得清楚?
版权声明: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,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。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,不拥有所有权,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/违法违规的内容, 请发送邮件至 举报,一经查实,本站将立刻删除。